本文不仅是对杨冬宝先生文化坚守的礼赞,更是对中国地域文化传承与价值的世界性表达。杨冬宝先生以文字为舟,以乡愁为帆,航行在淮安方言与民俗的河流中,捕捉那些即将消逝的文化基因。他所做的,不只是记录,更是一种文化生命的延续与唤醒。
越是扎根于土地的文化,越具有穿透时空的力量。淮安的方言、民俗、人情,虽源自一方水土,却承载着人类共同的情感与记忆——对故乡的眷恋、对根源的追寻、对身份的回望。这种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让我们看到: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从来都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瑰宝。这样的文化实践,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尊重与传播——既在中国,也在世界。
——加拿大红枫林传媒集团董事长 谷剑云
杨冬宝先生是我的挚友,亦是我的老师。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受过他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淮商传奇》中需要引用和沿用大量的淮安方言俚语,并且要准确表达,杨冬宝先生功不可没。他散见于各个地方的关于淮安民俗、方言、俚语的文章,给我助力颇深,为我的作品增添了别样风采。在文学和文化上,杨先生为我师。
同为地方文化的爱好者和探索者,在日常的交往中,我与杨先生相识已有二十年,每次相遇都有谈不完的话,每次分别颇有恋恋不舍之憾。在日常交往中,杨先生视我为忘年交,此即为友。
杨冬宝先生年长我十余岁,他高中毕业及大学毕业之后深耕于教育领域,是我这个教书匠的同行前辈,而在文化文学领域,他更是很早就开始着手整理淮安当地文化民俗,妙笔生花,整理成文,在各个媒体发表,而对于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写作者而言,无疑又是同行前辈。
亦师亦友,又是同行前辈,总是杨先生对我提携爱护较多。对于先生的作品,我是丝毫不敢怠慢的,每每有佳作问世,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阅读、勾画、做笔记……一遍又一遍,文章并不深奥,相反很容易读懂,而总能引人入胜,这一点是一般的写作者的作品无法达到的。整理书架的时候,整理到杨先生的书是最令人伤脑筋的事,一本是《人文朱桥一百年》,另一本则是《淮安俚俗口语汇释》。这两本书是如此魔幻,以至于书拿在手里,随便翻几页便彻底放不下了,书架也不整理了,开始了全身心地投入阅读,直到读完一本。
另外,还有一本电子版的《汉字玄机及其文化》,它也是杨先生学术探索与文化传承的结晶,为我们深入理解汉字背后的文化提供了独特视角。
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诗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对家乡土地热爱的大门。杨冬宝先生就是这类人吧。杨先生出身乡野,早年在乡间任教,在乡镇任职期间,亦未脱离乡村,是真正的“土生土长”的淮安文化学者。他对于乡村极为熟悉,对于淮安地方的民俗,有了最直观的感受和认知。他又是个极为有心的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淮安方言俚语中蕴含的丰富的地方文化,渐渐加以整理,集腋成裘,佳作频传也是情理之中。所以,他的作品中自然迸发出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凝练出的沉甸甸的土地的厚重,还有已经渐渐失传的丰富的地域文化印记,无一不诠释着这个文化学者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爱。
我常常在想,人什么时候会有乡愁?为什么会有乡愁?对于一个不曾长期离开家乡的人而言,他也会有乡愁吗?我也曾经跟几位文友深层次地讨论过这个话题,然而莫衷一是,最终没能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
在读完杨先生的作品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小时候,离开母亲视线的地方即为远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小孩子不愿意上幼儿园,不愿意上学了。因为要离开母亲的关爱和呵护,来到一个充满了未知的陌生环境,必然新生恐惧,这种恐惧让幼小的“乡愁”油然而生;成年后,我们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离开之前生活学习的地方,或近或远,身体离开了,心理却很诚实,乡愁会依然存在。
我的一个好友,从乡下来到县城,不过十几公里的路程,每个周末都要回乡下看望父母,雷打不动。我想,这是属于他的乡愁吧。那么,究竟什么是乡愁呢?是乡村邻里之间关切的话语,是家家户户熟悉的饭食,是一样的劳作场景,是那些流传于故乡的传说,那些历史上的风流人物,还有那一砖一瓦的古迹和遗存……无论你离得远近,在外定居还是暂住,总会收到一句“回来了?”这是对于在外生活的我们的关切,这就足够我们“乡愁”了。
而属于淮安人的乡愁呢?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乡音俚语,是那些几近失传的市井“暗语”,是那些乡亲们挂在嘴边的俗语,更是那些你也许已经忘却很久,提起来又恍然大悟且必然会心一笑的、独属于淮安的方言!
常年在外奔波,自然得说普通话。在夜深人静、独自一人在外地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多久没有说过家乡话了?事实上,即使在淮安,尽管说着一口浓浓的淮安话,到了乡下老家也会被认为“生分”。也许我并未在意,总倔强地认为自己说的是地道的淮安话,标准的“淮安腔”。可在乡亲们看来,我只是用淮安的音调说着让他们半懂不懂的普通话罢了。这一刻,我仿佛成了那个“君子固穷”“多乎哉?不多也”的孔乙己,就差问乡亲们“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了。
这些都是我读到杨先生的书之后所想到的。我们生在淮安,长在淮安,生活在淮安,我们真正了解淮安吗?恐怕不尽然。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淮安人,在市区住得久了,尚且与乡村的语言有了隔阂,那些背井离乡的淮安人呢?恐怕距离淮安更远了吧?因此,乡愁不仅有与故乡在空间上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距离。心理距离近,如杨冬宝先生,也许他并不感受得到乡愁的困扰;心理距离远,即使身在家乡,也会有乡愁,恰如我因为语言上的隔阂,却也产生了乡愁。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好比成年后你遇到一位儿时的玩伴,彼此多年未见,那种既亲切又熟悉的陌生感,让你们在短时间内都难以适应。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时代的进步,这是语言的进化,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也许这种说法有其理论支撑,毕竟连宇宙都是熵增的,遑论一个小小地区的语言文化和风土人情呢?然而,仅从我内心的感受来讲,我并不希望如此!我希望我的家乡能保持独有的风土人情,希望家乡的人们能熟练运用自己的方言,准确表达意愿和想法,希望我能与故乡的人们无障碍地交流沟通,我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当孩子们熟练地操着普通话交流的时候,当他们回到老家已经无法听懂乡音的时候,当我们能看到的淮安风物最终化为一缕历史的尘埃的时候,当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老去的时候,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记忆,包括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否都会烟消云散?
一个地方最显著的特色是文化,其次是饮食,最终归于地域文化。而在现实的信息爆炸的背景下,地域文化的生态无疑是最脆弱的。而地域文化一旦受到外来文化的侵入,其生态体系瞬间就会被肢解,想要再次恢复,几乎不再可能。也许再过几十年,淮安有一大半的人只会讲普通话,再也记不起淮安的历史遗迹,那将是怎样的悲哀。有人会说,其实这样也不错,更有利于交流,有利于淮安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然而,这样一来,淮安却会失去自身特色。一个没有特色的城市,还有什么底气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呢?
我始终认为,杨冬宝先生是伟大的,他敢于向所谓的“自然现象”说不!硬生生用自己的双脚,踏遍了淮安的每一个地方,走访了一个又一个乡村,采访了一个又一个的乡民,查阅了海量的资料,完成了两部在淮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对淮安文化的详尽记录,定格了淮安的过去和现代,更标注了淮安的未来,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两部作品足以浸润我们的心灵,抚慰我们的乡愁,追思我们的过往,继承我们的文化,这便是杨冬宝先生作品的意义。
我深感欣慰,我们淮安有杨冬宝先生这样的人,他才是真正最热爱家乡的那类人!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家乡的挚爱。他用一个又一个的方块字,诠释着运河之畔这个古城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颦一笑,一语一言!他用自己的笔触告诉世人,也告诉未来的人,在淮安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曾经有一群人,说着这样的方言,做着这样的事,勤劳、善良而淳朴地生活着。
我十分幸运,能有杨冬宝先生这样的师友。我从他的作品中读到了他的内心,读到了他的情怀,跟着他走过了一场令人拍案叫绝的淮安文化之旅。让我们的乡愁有了排遣之处,让我们的内心和灵魂有了归宿。
我很感谢他!我们都应该感谢他。
【责编 李媛】
《中华英才》半月刊网2025-10-10
《中华英才》半月刊网2025-0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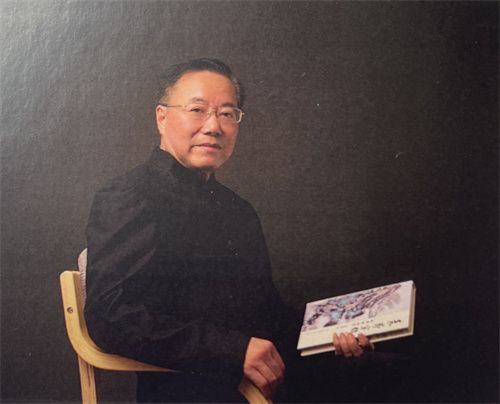
《中华英才》半月刊网2025-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