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之上,钢铁巨龙横卧,承载的是半个多世纪的光荣与梦想。
站在丹江口大坝的坝顶,俯瞰脚下汹涌的江水,难以想象这座“大国重器”是在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艰苦年代里,依靠十万建设者的肩挑背扛筑起的。坝体青灰色的混凝土在阳光下泛着光泽,仿佛在诉说着六十多年的风雨历程。

这座大坝始于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时的一个宏伟构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1958年9月1日,在荒山秃岭、荆棘丛生之地,十万建设者汇聚丹江口,依靠原始工具,“土法上马”,开启了这场战天斗地的壮举。
丹江口大坝的建设历程充满坎坷。1959年12月,工程实现大江截流后,却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紧张的双重打击。苏联专家撤走并带走图纸,使工程陷入困境。
1962年3月,由于缺乏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的经验,加之受“大跃进”影响出现赶工、抢工现象,工程建设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与安全隐患,党中央决定大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

当时的技术条件极为简陋,建设者依靠的更多是汗水和决心。据史料记载;一位年逾八十的教授级高工杨小云回忆,她从1963年来到丹江口,亲眼见证了大坝从破土而出到一寸寸长高的全过程。作为唯一参加过丹江口大坝初期建设、运行期管理和大坝加高工程全过程的“活字典”,她深知其中的艰辛。
1964年12月,国务院批准丹江口工程复工,但受当时国力所限,决定分期建设,前期工程仅将大坝修建到162米高程。正是这种尊重客观规律的务实精神,使得工程在艰难条件下依然稳步推进。

大坝加高工程面临的世界级技术难题,是初期建设者难以想象的。如何在40年前建成的混凝土坝体上贴坡加厚、加高,并确保新老坝体协同工作?这道难题困扰着全球水利工程界。
“与传统水利工程不同,南水北调工程所涉及的许多软科学与硬技术都是世界级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技术负责人曾表示。
长江委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加高坝体直接浇筑,新老坝体结合面合理修整并以键槽加强构造作用 。这些键槽是初期工程建设时就在坝坡面留下的“伏笔”,为后续加高奠定了基础。
大坝加高采用了“厚泵实”方法。老坝面的碳化层需要去掉3至5厘米,然后打锚杆,采用微膨胀水泥,并严格控制温度。这种创新方案实现了新老混凝土的完美结合,被誉为“世纪之吻”。
周恩来总理曾称赞丹江口工程是全国唯一“五利俱全” 的水利工程。这座大坝的功能之多、效益之广,实至名归。

防洪是丹江口水利枢纽的首要任务。大坝加高后,汉江中下游的防洪标准由20年一遇提高至百年一遇。自初期工程下闸蓄水以来,共拦蓄大于1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92次,累计减免损失约620亿元,彻底改变了“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历史。
供水功能则是南水北调战略的核心。截至2024年,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已累计输水超687亿立方米,受益人口近1.15亿。北京城区80%以上供水、天津主城区几乎全部供水都来自丹江口。
在生态方面,工程通过生态补水有效缓解了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问题。截至2024年11月,中线工程已向北方实施生态补水超106亿立方米,许多曾经干涸的河流湖泊重现生机。
此外,大坝还发挥发电功能,装机容量达90万千瓦,年发电量33.78亿千瓦时。同时,水库蓄水后,通航条件改善,船只可直达陕西省白河县,航运价值显著提升。

丹江口水库的建设史,也是一部奉献史。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均州古城,在初期蓄水时没入水下;大坝加高蓄水,老集镇又整体搬迁至新集镇,库区群众经历了“三生三世”的迁徙。
数十万移民两度迁徙,渔民收网上岸,全域禁捕——他们的牺牲让“南水北调”不再是一项冰冷的工程,而成为一曲感天动地的精神赞歌。
如今,丹江口水库周边活跃着一群“守井人”。他们包括清漂队队员、志愿者等,负责清理水面漂浮物、捡拾垃圾、巡检等工作,确保水库及周边地区的洁净。丹江口水库Ⅰ类水质天数已超过220天。水库中桃花水母的频频出现,成为水质优良的最佳佐证。这些对水质极度敏感的“水中大熊猫”,用它们透明的伞状身躯,无声地印证着守水人的付出。
回望这座大坝,它锁住了曾经的苍龙,化作润泽北方的清泉。而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已拉开帷幕,中线引江补汉工程施工正酣。这条蜿蜒于中华大地的蓝色缎带,将继续讲述着一个国家在水资源调配上的智慧与决心。
【责编 李媛】
《中华英才》半月刊网2025-1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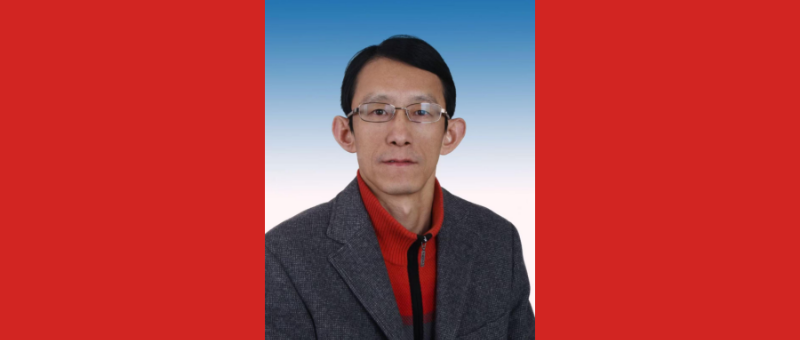
《中华英才》半月刊网2025-11-04
《中华英才》半月刊2025-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