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乃思
1966年出生,中共党员。现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繁昌区人武部义务新闻报道员。
笔者是土生土长的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孙村人,说起家乡自然如数家珍。但是,对梅冲村“塘口坝血战”这段红色历史的了解还是较长时间停留在表面。今年初夏,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在漫山野花争艳的时节,我和繁昌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课题组的同行们再谒塘口坝,通过走访、调研,发现这段腥风血雨、滚滚红尘的不平凡岁月有三个鲜为人知的细节。

乌龟山战斗“不做乌龟”
《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次印刷)第60页,对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梅冲村“塘口坝血战”作了如下记载:“14日晨,第3支队第5团第3营对向赤滩行进之日军主动出击,打乱了日军部署,迫使其改变行进方向,日军相继占领了九龙石,乌龟山等高地。第5团第3营乘日军立足未稳,向日军指挥所九龙石高地发起冲击,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这里所指的“14日”是1939年11月14日,赤滩即现在的孙村镇赤沙社区,九龙石乌龟山即塘口坝的两处山岭。
这乌龟山本是个无名高地,在塘口坝的东南,与塘口坝隔一条几百米宽的稻田。山的东侧连着大青山,西侧靠近黄浒至赤沙滩的河道和大道,南侧是一片起伏山地,山顶部是一个椭园形的大园丘。它是3支队与144师接合部上的一道重要屏障,平时大家在这里搞防御作战演习,战士们看它光秃秃、园溜溜的像个大乌龟,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乌龟山。
“哒哒嘀——”一声声紧急集合号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指战员们纷纷跑步集合。马长炎同志边跑边喊营部的同志:“快一点啊,营部不要‘做乌龟’啊!”“做不了!”战士们坚定地回答。不一会,队伍就在一个大草坪上集合完毕。黑沉沉的天空,没有一点亮光,战士们互相摸索检查着携带的装备,大草坪上一片“噃噃、嗦嗦”的声音。马副营长给各连干部作了战前动员。他在简单地介绍了敌情后,指出:“这一次,敌人的兵力武器都要超过我们几倍,大家要做好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坚决打好这一仗!”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为了打好这一仗,我代表营党委给各连党支部提三点要求:一、共产党员、指挥员要身先士卒,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保证阵地指挥不间断,政治思想工作不间断;二、随时随地搞好战场的宣传鼓动,不断用各种战斗口号激励部队,不打哑吧仗,全营要把杀敌立功、多抓鬼子、多缴枪、保卫繁昌、保卫皖南、誓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叫响,使部队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三、战斗中各支部注意随时搞好组织调整,考察和锻炼骨干,保证部队不散。”
“打啊!把鬼子打下去!”战士们怒吼着。就在这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只听到“哒哒哒!”一阵震耳的枪响刚过,林昌杨连长那高大的身躯突然晃了一下,便沉重地倒了下去。通讯员赶紧扑上去,只见他的胸膛横穿过了一排机枪弹,殷红的鲜血把他身下的泥土都染红了。一排长看到连长牺牲了,眼里迸出了火星:“同志们!为连长报仇!坚决把鬼子打下去!……”“替连长报仇!打啊!……”战士们无比愤怒。
这时英勇的2排长与他所率领的3个班长都光荣牺牲了。战士们坚持着,没有了排长,副排长马上代理,副排长受伤了,班长指挥,班长副、班长牺牲了,战士出来代替,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继续坚持战斗。
大娘的饭团也出战斗力
下午三时,鬼子的攻势已经大不如前了。第5团第2营营长陈仁洪大声地鼓励大伙说:
“同志们!鬼子已经没有多少力量了。现在6团3营已经上了三梁山,我们要同他们进行捉鬼子缴枪比赛,一定要坚守阵地,把鬼子打到山下水塘里喝黄泥汤!”“坚决守住阵地!”战士们士气高昂,尽管许多人手上、脸上到处有血,但是大家仍然一动不动地守卫在阵地上。这时马长炎同志得知陈仁洪负伤,带了5连1个多排来接替陈仁洪的指挥,要陈仁洪马上下阵地。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仁洪怎么能下去呢?
新四军在塘口坝的浴血奋战,深深感动了繁昌人民,他们纷纷动员起来参战支前,抬担架,送弹药,架小桥,送茶饭,就连国民党繁昌县县长朱镜峨也感动得亲自带人抬着担架来了。乡亲们送来一担担饭菜,又冒着枪林弹雨把伤员和牺牲的同志抢抬下去,马长炎同志亲切地对乡亲们说:“乡亲们!现在敌人还在进攻呢!大家注意安全,等枪声停了再来吧!”“别说了,首长,你们这全是为我们,新四军同志出生入死,流血牺牲,我们还怕什么?”一个60多岁的老大娘,带着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提着满篮子饭团,蹒蹒跚跚地从山底下爬上来。老大娘不顾阵地上的危险,硬是把饭团一个个送到战士们手里,一边送一边说:“大妈没有好吃的。吃点饭团点心,好跟鬼子打仗。”战士们被这位英雄的母亲感动了,一个个接过饭团,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阵地上的枪声开始缓和下来,支队通讯员跑上来寻问陈仁洪他们的情况,并说谭震林同志(时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正在调6团3营支援。陈仁洪要他将这里战斗伤亡情况转告谭副司令员,并特别关照他不要说自己负伤。请他转告副司令员,他们一定能守住阵地。下午3点多,谭震林同志派支队作战参谋文盛生同志来,并命令陈仁洪立刻离开阵地到支队指挥所去。陈仁洪离开阵地到了坝钉山指挥所。谭震林同志正在紧张地观察敌情,见到陈仁洪的衣服被荆棘刮得破烂不堪,关切地询问陈仁洪的伤势和部队的情况,最后还嗔怪地说:“刮了花还对我保密哩!”催陈仁洪赶紧去卫生队治伤。到黄昏时,敌人的有生力量已大量消耗,再也没有进攻的能力,只派小股部队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到阵地前来拖尸、收集武器。
谭震林责斥顽固派
塘口坝战斗就这样以敌人的惨败和我军的胜利而告终。这次战斗,敌人前后投入的总兵力达2200多人,死伤400多人,川岛中佐指挥官被我军击毙。我军伤亡80余人,缴获大量步枪、毒气筒、信号筒、浮水器及各种弹药等。
塘口坝血战的胜利,伴随着战场隆隆的炮声,很快传遍了江南。当时,日军派遣军总司令不得不哀鸣:“国民军乃是手下败将,唯共产党乃是皇军之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党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新四军《抗敌报》为此发表了题为《保卫繁昌屏障皖南的伟大胜利》的社论,通报表彰了3支队和5团。国民党第三战区也不得不在全军通令嘉奖,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发出贺电。
战斗结束后,3支队在铁门闩的铁门庙召开总结大会,谭震林同志当着三战区“联络参谋”的面,责斥顽固派:“……塘口坝血战的事实,就是要让那些假抗日、真投降的人们看看,谁是抗日的先锋!他们说新四军游而不击,不能打仗;新四军血战繁昌,而他们自己却蹲在山上,连个屁也不敢放,骂新四军,帮鬼子说话,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听着谭震林同志激烈的怒斥,到会的同志非常痛快,只有三战区的“联络参谋”如坐针毡。远处还不断传来炮声,会议中不断又有敌情报告,搞得“联络参谋”们胆战心惊,他们坐在桌子旁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往日那趾高气扬的神气全都飞走了。
总结会结束的第三天,那些“联络参谋”突然打点了行装,来到谭震林同志的住处辞行。谭震林同志笑着挽留他们说:“怎么,诸位要走?塘口坝战斗之后,日军不会干休,以后的战斗会更大,欢迎诸位继续督导。”为首的“联络参谋”一听,急忙推辞说:“哪里,哪里,一年来属下随谭司令官转战皖南,亲眼得见贵军志诚抗战,坚贞不渝,令人钦佩之至。社会上说贵军‘游而不击’,实属流言。”谭震林同志说:“新四军将士浴血抗战,诸位亲眼所见,想必不会说不知道,只是希望你们回去以后,向先生们也说说这里的真实情况。”“联络参谋”们一听,连说:“那是,那是,一定,一定。”他们向谭震林同志请了一个长假,从此再没回到支队部来了。
顽固派们的无耻谰言被揭穿了,新四军在军事、政治上打了个大胜仗,威望越来越高,大大鼓舞了华中人民的抗战斗志。后来为了纪念这次难忘的战斗,人们还编了一首《繁昌之战》的歌子,在江南、江北到处传唱。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陈仁洪革命回忆录。革命前辈李一氓在作序时指出:“当时,仁洪同志任第5团第2营营长。我参加岩寺的新四军整编工作,因而我认识了他。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坚决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他们和八路军的同志一起,忠实地代表全民族的利益,高举抗战旗帜,浴血奋战。譬如第3支队就在皖南前线,作为繁昌七次保卫战的主力,打得敌人胆战心惊。其中塘口坝之战尤为激烈,至今回忆起来,战场景况,犹历历在目。敌我对垒,白刃肉搏,往返冲杀,我毙伤日寇约400余名,敌酋川岛中佐也被我击毙。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我军获得皖南抗战的伟大胜利,皖南人民群起欢呼。本书作者以营指挥员亲身参加和指挥了这次战斗。我主持的新四军《抗敌报》特为此发表了社论。社论高度评价这次战斗的英勇和胜利:‘只要看一看我们牺牲的同志一手握着手榴弹,一手握着步枪的情形,就可想见其壮烈坚决的斗志;只要看一看我们2营营长陈仁洪虽身受数伤,而犹指挥到战斗终结,就可以知道是如何保持和发扬了我们轻伤不下火线的传统。’今年是抗战胜利40周年,无论如何,我军8年抗战的历史勋业,已光荣地载入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史册。”
这些细节与感动并不遥远,它们就在一份份白纸黑字的史料中,只要潜心读罢,其中的人和事就会鲜活而厚重。正是它们,一日日地冲击着我,促使着写作与倾诉的冲动。
写作的冲动、起于感动、却不止于感动,更多的,是理性的思索,是传承的需要。笔者和同行们常常热烈地讨论着、联想着,因为这些人与事,可以追溯到古已有之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以及范仲淹追求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与今最大的区别在于、古人常常叹道,“微斯人,吾谁与归?”而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共产主义理想理念所锤炼造就的,正是这样的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
他们“不怕鬼”、有信念,能战斗;他们扛上历史的责任,担着国家民族的使命,向前看,不回头;党性在他们的身上,绝不是干巴巴的几句概念,而是如此生动、真实地存在着……
湾湾的塘口坝啊,红旗漫卷赤沙滩。在这里,每一个山冈,每一棵树木,每一条河川,都映照着革命先辈浴血奋斗的身影与雄姿。信手掬一抔土,你可闻得硝烟;摘一朵山茶花,你能谛听英烈冲向敌营的厮杀声……这就是塘口坝。这就是无数英烈为建立新中国而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漫山杜鹃的塘口坝。
从抗日战场到发展热土
时光虽然已过去了80多年,但今天我们在塘口坝调查,仍能时时感受到乡亲们对当年新四军那份纯朴的爱,我们更被一个普普通通的守墓故事所感动。
塘口坝血战之后,新四军将阵亡将士的遗体运至邻近的3支队司令部所在地中分村,裹上白布装殓入上好的棺木进行厚葬。随后,新四军一一联系阵亡将士的家人,并将遗骨陆续迁回各自的故里,唯独有一位5团4连连长李志坤烈士的亲人一直无法找到,他的坟墓只好留了下来。与烈士同姓的中分村一位孤寡老人李金泉,主动承担了看护李志坤烈士坟墓的义务。每年清明他都要上山扫墓,冬至为烈士焚纸祭奠,整整20年,从不中断。1959年,李金泉老人临终前仍然惦记着烈士的坟墓,他嘱托当时的生产队长代为看管,队长答应了老人的遗愿。1965年,繁昌县修建公路,对这座坟进行了迁移。时任中分村团支部书记的徐孝旺,正好在公路指挥部工作,他十分清楚中分村人民对烈士的感情,于是他特意打报告,向县民政局争取了专款,并于1969年在李志坤新的墓前立了一块石碑。这虽是李志坤烈士牺牲整整30年后补立的一块碑,但更加体现出中分村人民对新四军烈士的爱。随后,中分村又筹款两万多元,对李志坤的墓进行了修缮,并树立起了一个高大的花岗岩石碑。石碑上面刻有一颗红星和伟人的语录:“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梅冲村革命烈士艾国朴的后代艾和发,主动请缨当任村关工委执行主任。几年间,艾和发把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政治责任,深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教育,依托“五老”宣讲团,利用村史馆、塘口坝血战遗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红色故事宣讲教育,打造具有梅冲村特色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品牌。在大家眼中,艾和发是一个为了帮扶特殊儿童倾尽全力的人,通过思想上关心、情感上关怀、心理上疏导,着力为青少年成长办实事解难题。艾和发为关心下一代做着平凡而琐碎的工作。在他看来,青少年如同朝阳,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有了这份爱作支撑,他会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正是红色记忆、红色历史早已深深镌刻在这片热土上,激励着人们赓续传统、奋发图强的生动体现。
又一次走进梅冲村,登上乌龟山。那里曾经的枪炮声、怒吼声、杀敌声已被淹没在浩瀚的历史尘埃中。此刻的塘口坝古村,是一首山水诗。如何在保持古村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华丽的转身,让隐于大山中的自己想方设法走出去,热热闹闹地把四方宾客迎进来,必须让乡村振兴牵线搭桥。宁芜高速G4211繁昌西互通立交及连接线工程在昔日塘口坝战场上如火如荼地兴建,由此结束了孙村镇无高速出入口的历史,使人民群众几十年来盼望高速公路互联互通的梦想变为现实。它的建成,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巨变,无声地宣告着:老区人民正迈步在通往美好未来的征途上。这条现代化的交通大动脉,如同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纽带”,将梅冲村与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古村的“一片叶(梅冲白茶)、一坛油(梅冲溪花麻油)”等特色农产品变成一张张洒向神州大地的闪亮名片,造福村民,走出大山、誉满神州。
说到如今的梅冲村,村党总支书记情不自禁地说,梅冲村地形为“三山夹两冲”,至今已有550余年历史。随着“山道变赛道”连续两届全国山地自行车大赛在梅冲白茶园举办,艾家老屋、走马楼等多处清末、民国时期民居的保护修缮,以及“山水梅冲,十里画廊”的旅游休闲、生态宜居村庄的打造,梅冲村已列入全镇“马梅长红”精品旅游线路之一。先后获得安徽省首届美丽茶村、安徽省生态村、安徽省森林村庄、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芜湖市乡村振兴示范村、芜湖市人居环境示范村、芜湖市首届文明村、芜湖首届魅力乡村等荣誉称号。看他那神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爱梅冲村犹如爱自己的孩子一般。
赤沙河在默默地流着,穿村而过。我凝望着眼前幽深的河水,回想着在塘口坝的所见所闻,心中泛起阵阵涟漪。我在想,悠长的河水流走了岁月的泥沙,却流不走凝固的历史。而凝固的历史与流动的现实在这里交织,或许后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注吧。漫步在塘口坝的土地上,感受着历史与现实的交融,心中不禁涌起无限感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变迁;这里的每一个故事,都诉说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从当年的战火纷飞,到如今的繁荣昌盛,塘口坝的发展历程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写照。作为一个匆匆过客,笔者祈愿塘口坝的明天更加祥和美好——这是老区人民的福祉,也是历史最好的纪念碑。
新四军3支队的源头是闽北红军游击队,而闽北、闽西是方志敏等红军将领长期战斗过的地方。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党迅速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十月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苏南、皖南等抗日前线。闽北的红军游击队,就集合到皖南徽州岩寺,成为新四军的一个支队的一个团,即新四军第3支队第5团。而在此前的1934年11月,方志敏被任命为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领所部执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使命。方志敏说:“为了可爱的中国,为了民族的生存,我们就要离开亲爱的苏区了。目前革命虽然受到了挫折,但是,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相信久经战斗的闽浙赣人民一定能克服困难,坚持斗争。等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还要回来。这一天,决不是很久远的将来。”(源自《中共横峰县地方史》)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方志敏烈士在《可爱的中国》中如此写道。看一看眼前的梅冲村塘口坝,从抗战之地到和美乡村,水清、岸美、鸟飞、鱼跃,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这不正是方志敏烈士心目中“可爱的中国”的一个缩影吗?
【责编 李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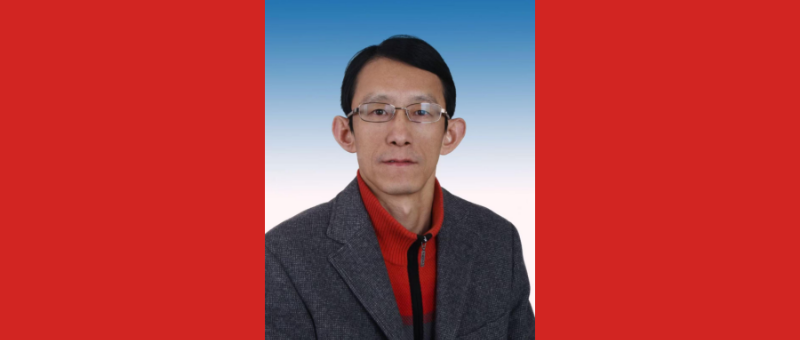
《中华英才》半月刊网2025-11-04
《中华英才》半月刊2025-11-04
《中华英才》半月刊网2025-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