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简介:
诺布朗杰(Norbu Namgyal):男,1989年出生,甘肃甘南人,毕业于兰州文理学院中文系。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南藏族自治州作家协会副主席,舟曲县作家协会主席。甘肃省文艺创作传播中心首届签约作家。著有诗集《蓝经幡》《藏地勒阿》《拾句集》。

王选:诺布朗杰兄好,你在甘南,我大多数时间在兰州,咱们好像仅在今年定西一次活动上见过,也是匆匆一见,便各自散去。咱们在线上倒是因参加活动见过,不过次数也寥寥。我印象中你是90后,做这个访谈,才知道你是1989年出生,比我略小。说到年龄,你觉得年龄,对于写作意味着什么?
诺布朗杰:我一直觉得,30岁是个年龄的分水岭,当自己的年龄真的到了30岁的时候,好像给自己定的目标很多都没能完成,又给自己延续了5岁。现在我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现状,有重重压力,写作的宝贵时间也会都被生活里琐碎的事情瓜分。好的一点是,我现在能沉下心来了,也没有二十出头时的毛毛躁躁。
王选:35岁,已不再年轻,到了上了老下有小的时候,生活的担子挑在肩上,两头都重,我们都在生活的大雨中,正如你说“就算躲进大巴车里,仍绕不开尘世的茫茫大雨”。你在甘南生活,有些作协的朋友可能都不大了解,能介绍一下你的生活吗?
诺布朗杰:我大多数时间在舟曲县城生活。母亲,两个孩子,还有爱人。能算得上其乐融融吧!刚结婚时,出现过一些矛盾,经过几年的磨合,家里很和谐。“就算躲进大巴车里,仍绕不开尘世的茫茫大雨”,这是组诗《甘南,或鹰的诗篇》里的诗句,是我对我当下生命的体验。
王选:你的诗歌中,很多是写给勒阿的,勒阿是你的故乡吧?给我介绍一下这个村落,它对于我们理解你的诗歌应该有帮助。
诺布朗杰:是的。写我的家乡勒阿村的诗歌偏多。勒阿村属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果耶镇管辖,纯藏族村落,目前有100多户,勒阿村是滋生我诗歌的土壤。我诗歌里很多篇章都材取于勒阿村。近几十年,勒阿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用文字记录着关于勒阿村的一切。我的诗歌不是山水美文,里面有更多文化层面的反思。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用当下的眼光去看待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只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时间轴拉长一点,就会漏洞百出。处理素材时,我很警惕。
王选:你的故乡勒阿,于你而言,与你的写作而言,有什么意义?
诺布朗杰:与给我童年的那个勒阿相比,现在的勒阿似乎是另一个勒阿。我写故乡勒阿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我的诗歌,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勒阿,改善勒阿村的交通和一些基础设施。我也没想过故乡对我及我写作的意义,坚持写下去,意义会不会自己就呈现出来了呢?
王选:你现在应该在县城工作,县文旅局是不?平时工作如何?具体做哪些工作?
诺布朗杰:舟曲县文旅局。我主要做的是剪辑视频,维护单位的微信公众号。单位上的工作比较琐碎,比较杂。处理一些文件,有时候还得写一些解说词,各类发言材料什么的。我还是能得心应手。干工作不难,干好工作才难。
王选:在县城生活,离开了勒阿,平时经常回去吗?在城市和村落这种有着隔阂地域,你如何平衡写作,如何面对种城乡之间的疏离?城乡二元结构有没有给你带来内心的冲突?
诺布朗杰:很少回勒阿。我生活的小县城舟曲和勒阿村没太大的隔阂,我感觉舟曲县算不上什么城市,现在的农村反而很阔气。从舟曲县城到勒阿村,也就一个小时的车程,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基本一样。在勒阿村与在舟曲县城的区别不是很大。离家乡越远,这种疏离感才越强吧!
王选:我看有篇介绍你的文章,说你不会写藏文,只会说藏语,你身上大约有60%藏文化,40%的汉文化,这两种文化对你而言,有何意义?
诺布朗杰: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在舟曲县城关一小上学,没有学过藏文,所以不会写藏文,只会说家乡的藏语。从小学五年级到大学毕业,我系统地学习汉语,接触汉语。当时我给诗人白朵说:我身上大约有60%藏文化,40%的汉文化。这个比例现在应该反过来:我身上大约有60%汉文化,40%的藏文化。两种文化对我的意义是:用藏文化走路,用汉文化说话。
王选:你的写作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诺布朗杰:高中时候有写诗的冲动,写作应该是从2010年在兰州文理学院上学期间开始的。
王选:你在兰州上学那会写诗,参加活动,应该是一段青春期的黄金时代,给我说说那段经历?
诺布朗杰:怎么定义在兰州上学期间参加各种与文学活动的有关的经历呢?那段时间我反而没写出什么诗歌。当时我们的口号是“把边缘化的文学带到时代的中央”,把文学有没有带到时代的中央不得而知,差点把自己带沟里了。每年我们会联络甘肃各高校的文学社团组织很多文学活动。不是搞活动,就是在搞活动的路上。我察觉到写作的意义要大于搞活动的意义,之后,我也慢慢淡出了熙熙攘攘与吵吵闹闹,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现在回想那段时光,还是一段不错的回忆。
王选:因为什么原因开始写诗?
诺布朗杰:父亲喜欢文学,受父亲的耳濡目染,很早接触到了诗歌。
王选:在你的诗歌中,很多都是在写甘南这片神奇、深邃的地方,也可以叫做藏地诗篇,谈谈你的这些作品。
诺布朗杰:我90%的诗歌都可以叫藏地诗篇。很多的诗歌还是很稚嫩,挖掘的深度还欠火候。有老师给我提出我诗歌的缺陷,缺少当代性,语言陈旧等等问题,我欣然接受,也想方设法克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写作水平不是一朝一夕提高的。我的诗歌良莠不齐,不乏有好的作品,但差的也不少。
王选:读你的诗歌,总让人安静,和同时代的甘肃诗人相比,你的诗歌是有自己面目的,你觉得和其他人相比,你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诺布朗杰:我的诗歌创作也属于就地取材吧!我好像只能处理自己亲历的素材,很少在行文中用间接经验,这个应该是与甘肃青年诗人的独特之处吧!我写勒阿,像《日赤活佛》《年卜热桑神山》《次曲神湖》《穷喇嘛》等诗歌,都是取材于勒阿村的传说故事,有些地名还是我确定的,首次在我的诗歌里用了这些新词汇。
王选:在你的诗歌中,有一些仿谣曲,短而生动,很有意味,谈谈这些诗歌?
诺布朗杰:之前有写系列仿谣曲的打算,写了近十首,越写越顺。我沾沾自喜地跟我的诗人朋友吕达分享过“情歌”系列,听了吕达的忠告,我放下了继续创作的念头。那些诗还是缺乏诗歌的内核。
王选:在你的诗中,我读了一些淡淡的哀愁,还有在草原独处时的思考,不知别人有没有提及过?
诺布朗杰:生活中我嘻嘻哈哈,写诗的时候我很严肃,我是个悲伤的诗人。不用别人告诉我,我自己也能感受到,我不喜欢把稍纵即逝的幸福写在纸上。把幸福留在纸上就的是晒、是炫耀,把不幸与疼痛留在纸上,才是诗、是生活。孤独、悲伤、眼泪,这些是我所理解的生命的原色。
王选:甘南有一批优秀的诗人,平时你们接触多不多?交流诗歌、文学多吗?
诺布朗杰:接触不多,都在忙自己的事,有征稿或文学活动的时候,会畅谈文学。
王选:你如何看待甘南诗人的写作?
诺布朗杰:李志勇老师、阿信老师、完玛央金老师、牧风老师、扎西才让老师、瘦水老师、嘎代才让老师、花盛老师,他们的诗歌写得非常棒,都有自己拿的出手的诗歌作品。甘南诗人的势头很好,我们这些年轻诗人还是接不住老一辈诗人手里的接力棒。
王选:在草原、经幡、鹰、牦牛等这些共同的意象中,如何保持自己诗歌的独特性,而不和其他甘南诗人重复?
诺布朗杰:写的独特不难,写出新颖才难。您说的“诗歌的独特性”指的是语言的辨识度吗?还是指写作风格?有语言的重复,有内容的重复。诗歌不同于其他文本,它的体量小,做到语言的高度凝练不容易。十句话的问题一句话能表达清楚的,就是诗歌。长期的写作,慢慢就形成的自己的某种特点。那些共同的意象,表达的点不同时,呈现出来的也是不一样的。我不刻意追求独特性,或者避开重复。
王选:谈谈你的几部诗集,当然还有散文诗创作?
诺布朗杰:能自己不掏腰包出诗集,是我们这些三流诗人的荣幸。第一本诗集《藏地勒阿》多亏了苏木素老师的资助,当时树贤也忙前忙后做了很多编辑工作,我记得诗人朋友西克专门为我们12位青年诗人的诗集设计封面;第二本诗集《蓝经幡》是在鲁迅文学院上少数民族培训班期间敲定出版的,还是得口头感谢鲁院的老师们;第三本诗集《拾句集》是武汉卓尔书店资助的,翻看的时候发现了好几处问题,但我还是觉得是个不错的集子。
散文诗一写就停不下来,沉迷到散文诗创作,甚至不想写诗。我的散文诗在能发表的水平,你让我拿出一篇能代表自己散文诗创作水平的一篇,我都拿不出来。写好每一种文体,都不太容易。
王选:甘肃老一辈诗人的诗歌平时阅读吗?对你有没有影响?
诺布朗杰:以前读了些甘肃老一辈诗人的诗歌,还购买过早期出版的《甘肃的诗》,读了很多甘肃诗人的诗歌。伊丹才让的诗歌系统地读了,李老乡、高平的诗歌也读过。尤其是伊丹才让的诗,坚定了我诗歌创作的决心。
王选:甘肃青年诗人的作品阅读不,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诺布朗杰:没有系统地读过,微信公众号上零零星星地读了些。我的水平还不足以梳理咱们省青年诗人的优点和缺点。让杨光祖老师谈甘肃青年诗人的作品优点和缺点,肯定会让甘肃青年诗人得到更多的启发。
王选:有人说,你写歌词跟你的“丑”有关。你从小热爱唱歌,并且嗓子也很好。但是自从发现自己很丑以后,就不打算唱歌了,谈谈你的歌词创作,大家可能也感兴趣。
诺布朗杰:哈哈!也不全是。主要是我喜欢做一些幕后工作。2014年由我填词的歌曲《天上果洛》被藏族著名歌手谢旦演唱了,当时,我非常激动。文字被朗诵一种感觉,被唱出来,又是另一种感觉。后来跟水木年华的卢庚戌老师一起合作了《忘不了就别忘了》《感谢生活》《唯你一生》《失败者之歌》等歌曲,其中《失败者之歌》改编自我的诗歌《鹰的诉说》,起初歌名叫《坠落的飞鸟》,后来商定为《失败者之歌》,与《感谢生活》一起收录到水木年华音乐专辑《手里的吉他是治愈世界的伤》中。这也是文字的另一种尝试。
王选:诗歌和歌词,你怎么看待这两者?
诺布朗杰:用歌养诗,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诗歌小众,纸媒缩减,稿酬微薄,这些都会使诗人们走向绝境。
王选:在你的写作中,我想母亲是很重要的,我看到一个细节,她对文字的敬重,你觉得,在的人生里,她给你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了什么?
诺布朗杰:母亲只上过五年级,但是母亲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我的有些诗歌母亲也读,一定程度上,母亲还是我的读者。所以,我的诗歌里,我会避开很多露骨的内容。怎么说呢!我的诗歌内容比较健康,老少皆宜。
王选:现在有几个小孩?平时谁带?影响写作吗?能在孩子身上得到什么?比如纯真、快乐、责任。
诺布朗杰:两个男宝宝。妈妈、媳妇、我三个人换着带。会影响写作。由于有了小孩,我就有了写儿歌的想法,也参与一些儿歌创作。我与音乐人郭志凯老师合作的儿歌《月亮妈妈》《小小稻草人》《小小的台灯》《勇敢的猫》《打捞彩虹》等,都还挺不错的,给你推荐一下!有了孩子以后,我竟然还有了写童诗的冲动。
王选:现在在阅读什么书?写作什么内容?
诺布朗杰:《让我们相信这寒冷季节的黎明》(芙洛格·法罗赫扎德著;李晖译),《红色手推车》(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著;李晖译)。参加了好几次采风活动,准备采风作业。
王选:最后一个问题,你的写作理想是什么?
诺布朗杰:我希望自己能驾驭长诗写作。
王选:你曾是诗中写到:“走得慢,才能到”,这句话很有理。如果热爱,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急不到哪里,所以慢慢走,才能到。咱们就聊到这里,谢谢,以后有机会,再做探讨。
诺布朗杰:谢谢您!“走得慢,才能到”是母亲的原话。慢慢走,希望我们的每一步都走得很好。
诺布朗杰诗歌10首:
《次曲神湖》
次曲收走了她唯一的儿子。母亲哭了三天三夜
眼睛哭瞎了,也没能把儿子哭回来
盲母每天都去哭。久而久之,打动了次曲神湖
一次,盲母在次曲神湖边睡着了
突然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人给了她一捆柴禾
她顺手拿了一根,当拐杖
等她醒来,发现拿的那根木棍,是银质的
盲母心动,去次曲神湖边找。可惜再也没找到
《在勒阿写诗》
在勒阿写诗,我是轻松的。可以不用过多炫技
只要母亲能看懂,就可以了
我不写青稞地。青稞地白白地荒着,那些杂草
像我的情绪,盘根错节在诗句中
不写牛羊,山坡上已无牛羊。现在我还把它们
入诗。我的诗就显得空洞、乏味、做作
被人们排挤的旧寺,脱下的藏服,丢弃的母语
这些我都不写了。我怕我的诗歌黯淡无光
在勒阿写诗,我也是痛苦的。我巴不得掏出
我的心。让你们瞧瞧
《勒阿女人》
她们目不识丁,但她们知道土里生金
她们说:山里的青稞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
男人虽是家里的顶梁柱,却又靠不住
好不过一块出粮的田
好女子不出庄,好骡马不出庄。
她们说:她们就是地里长出来的庄稼
《守灵人的夜晚》
他是一堆孩子的父亲
在今晚,他是丢失父亲的孩子
他被淹没在一群守灵人之中
默不作声
他给来家里帮忙的人,分发着
体面的香烟
夜晚如此漫长。他掏出
一包廉价的烟
深深吸了一口
《洛扎老人与刀》
好木头要雕佛。洛扎老人的刀口上
是慈眉善目的佛
剩下的木头要雕念珠。念珠上
是洛扎老人的刀,走的路
无用的木头雕根拐杖。再不雕
洛扎老人像用旧的刀,越来越钝了
《果耶小镇》
2018年,果耶撤乡建镇。现在大家才可叫果耶小镇
果耶并不小。我们去任何地方,都要经过这里
八岁那年,我随父母经过果耶。第一次见到白龙江
我忍不住喊出声来:快看!大海!大海!
后来,我多次经过果耶。那时候爷爷总是带着我走
我还是孙子。我的世界就果耶那么大
再后来,爷爷谢世。剩父母带着我从果耶来来回回
果耶仍叫果耶,爷爷像龙江水流走了。我成为儿子
我路过果耶,常听说一个个人像白龙江水一样流走
他们或许成为另一个自己,在另一个地方继续活着
有人从这里回来,不走了。有人从这里离开,不来了
也有人生在这里,死在这里。一辈子与果耶为邻
现在是2019年,我反反复复路过这里。再过几十年
我的孩子又要替代我路过。那时,果耶还会叫:果耶
《诗是随身携带的故乡》
我的故乡寄居在狭窄的纸上
我多想把我的故乡,从狭窄的纸上解放出来
可我办不到
我只能在纸上,复原故乡
故乡突然缩成了一枚针,正在戳我
我忍不住在诗里哭出声来
诗,故乡;故乡,诗
我把它们混为一谈
我呼吸,好像故乡在呼吸
我叹息,好像故乡在叹息
而诗呢?
诗是我随身携带的故乡
《口弦》
竹子做的口弦,有流水的声音。少女们弹爱情
妇女们弹生活。男人们留下来,做口弦
口弦好弹,情话难说。你再不说,未婚的女子
就都一个个要嫁人啦!
你有老虎的胆;你有鹦鹉的舌;你有蜜蜂的嘴
可你到底有没有自己,一颗真诚善良的心?
悲伤的人把悲伤留在口弦上。快乐的人把快乐
留在口弦上
像我这样不痛不痒的人,没什么可留在口弦上
只能把一首写坏的诗,留在口弦上
《勒阿短句》
我把母亲留在了勒阿
你们如果想看我的母亲
我就给你们推开那座山,推开那片森林
我把父亲留在了勒阿
你们如果想看我的父亲
我就给你们挪开那片雾,挪开那场大雨
我把我留在了勒阿
你们如果想看我
我就给你们拆开我的诗句,拆开我的词语
《想留下活着的诗》
我一再确认:我有没有活着
我其实是在确认:我的良心有没有活着
我的正义,我的善良,我的勇敢有没有活着
我饱满的爱有没有活着
我因爱这个世界而产生的恨,有没有活着
如果这些中的某一个死了,我就真的死了
我留下的诗估计也是死的
我一再确认:我会不会死去
我其实是在确认:我的眼泪会不会死去
眼泪是眼睛说过的最动人的话
好多人正在受难,我竟然不愿为他们流下泪
我竟然向弱者抡起拳头
我竟然又向强者点头哈腰
很显然,这时候我就真的死了
我留下的诗也一定是死的
想留下活着的诗,很简单。你必须得有一样
是活着的
【责编 丁鹏】

《中华英才》半月刊网2023-09-04

《中华英才》半月刊2023-08-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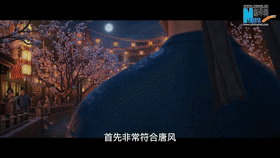
新华网2023-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