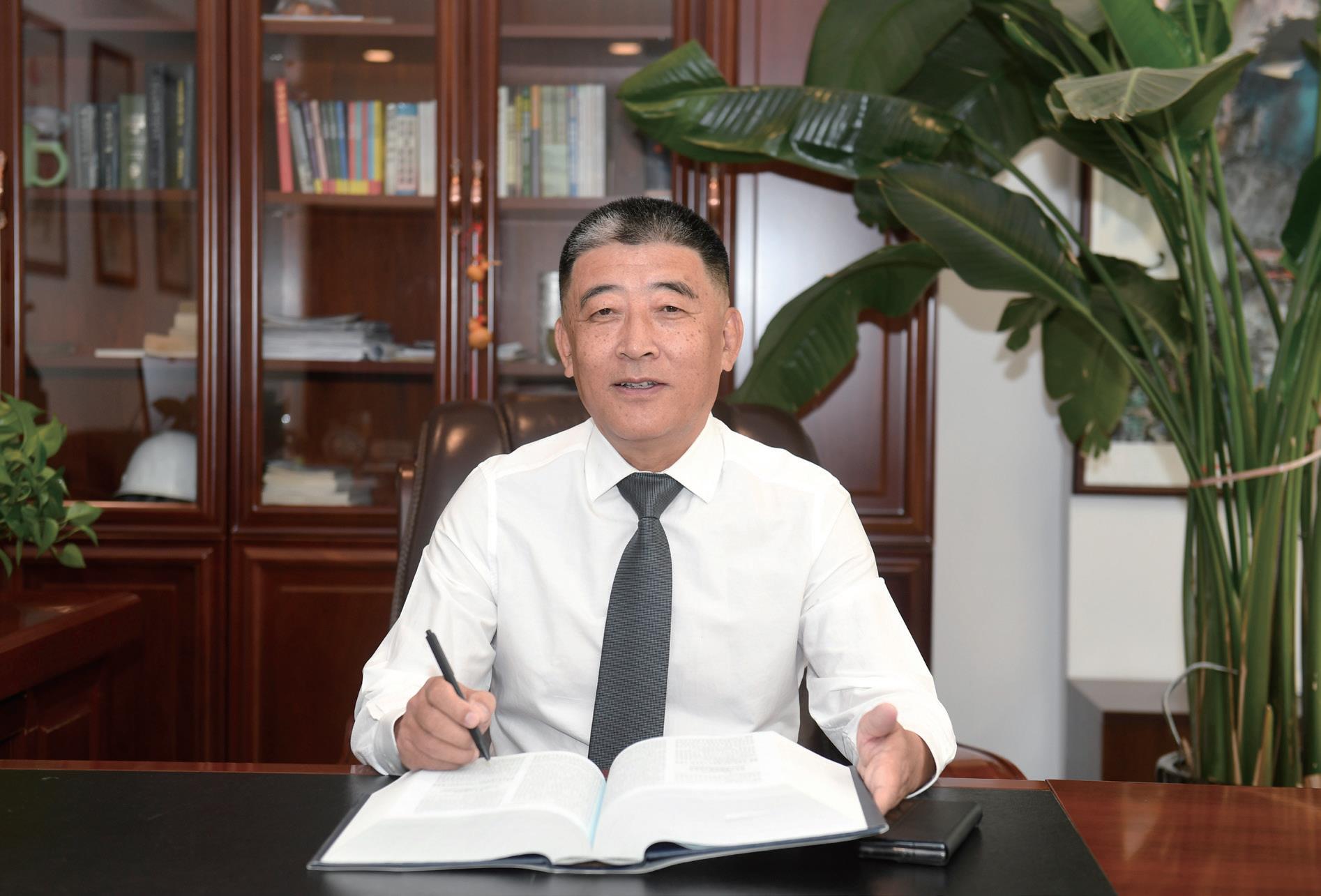朱虹璇:只为告诉你,初衷是多么重要
 大字号
大字号非职业戏剧团体“话剧九人”一路坎坷走过10年。去年九月,他们的《四张机》《春逝》《双枰记》三戏连演,热门网络平台评分分别是8.6、8.7和9.0。
做话剧,始于“江湖救急”
在吃散伙饭的时候,一群人都喝得有点大,又想到马上要毕业了,推杯换盏间就有人说:“现在我们演这样一个戏,二十多岁,演的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要不我们连演十年吧,演到我们都三十来岁,正好是剧里面人物的年龄,再去演绎哀乐中年。”已经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最先提出这个提议,大家当时喝得都有点高,都很高兴地说“好啊好啊,连演十年”,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那时,正是朱虹璇北大研究生即将毕业的时候。
朱虹璇,是“话剧九人”的编剧、导演及创立者。“话剧九人”当时算是在学校里跟朋友们一起做的一个社团,到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坚持演出十年,年年有戏,观众越来越多的正式剧团了。
朱虹璇形容“话剧九人”有三个关键词:十年、三无、双打。“十年”,代表着话剧九人以作品进行的编年,“2012年是我们的第一部作品,一年一部原创,到去年是第十部,正好算作我们的十周年。”
“三无”则是指剧团“既没有官方背景,也没有流量加持,更没有‘金主爸爸’,完全是一个民营个体户,所以经常自嘲是‘三无组织’”。
至于“双打”,朱虹璇的解读是,“我们团队里既有职业戏剧人,也有一些有另外一份本职工作或是还在读书的朋友,是一个非职加职业的‘双打’模式。”
朱虹璇开始做话剧的原因特别简单,“2012年还在学校里,我有一个朋友,报名了北大的剧星风采大赛,他担任的职务是编剧。可马上要交剧本了,他只写了六行字。于是,从来没有写过剧本的我就这样被抓去,临阵磨枪上了阵。”
当年的朱虹璇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原创话剧,所以选择了改编美国一部黑白电影——《十二怒汉》。这部电影讲述了十二个陪审员决定一个小男孩生死的故事。
因为剧星风采大赛每个剧目只有四十分钟的表演时间,所以朱虹璇需要把两个小时的电影改成一个四十分钟的剧本。 “于是就把十二个角色改成了九个,这就是我们第一部剧的名字,《九人》,也是我们这个剧团名字的由来。”
“九人”这个名字也被沿用到了剧团后来的很多部原创话剧上,直到2018年,才开始给每个作品独立命名。
酒后“胡话”,约定成真
最初那部《九人》,在北大剧星风采大赛上走到复赛,输给了当年的总冠军。大家都很不舍,于是在吃散伙饭的时候,就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个酒后相约“连演十年”的故事。
然而酒桌上说过的“胡话”并未被大家忘记。2014年,已经毕业、走向各行各业的“九人”们,又开始聚在一起做戏。
朱虹璇仍然担任编剧,她找到了导演莫小巧,导演又去找了灯光、道具……最终攒起了一个团队,尝试商演。
“这和在学校参加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走向社会,公开演出,要有票房,中间涉及到的环节非常多。要找场地、找人员、配演员、排练、做道具、宣发卖票,很多琐碎的环节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朱虹璇记得,2014版的《九人》是在北京的蓬蒿剧场演的,只有八十多个座位,就算人都坐满了,也很难在票房上回本。所以那一年他们大概亏了有三千多块钱。“当然我们的总成本也就六千多块钱。”朱虹璇笑起来,“毕竟,当时的舞美基本上就只有凳子和桌子。但那天我站在侧台,看到结尾,灯光慢慢暗下去时,心里还是觉得‘很值’。这或许就是戏剧的魅力吧。那一年的戏,虽然只演了一场,也亏了钱,但是剧场里与观众那种真诚的互动,给了我们信心,让我们觉得从学校走出来,去真正面对社会上的观众,还是有可以做下去的希望的。”
剧团之后的几部戏都叫《九人》,但是每一年其实都是一个全新的故事。比如2015年的《九人》,讲述了公交车上的一场争论;2016年,一家日薄西山的纸媒陷入理想和现实的困境……
粗糙的开始,渐进的道路
朱虹璇还清楚地记得2015年的演出:“很不好意思说它有舞美,那其实就挂了几扇用纸糊的窗户。我记得当时第二天要演出了,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在糊那个纸窗户。它是用鱼线吊在灯杆上的,演出的时候就肉眼可见地逐渐下坠,最终不负众望地掉下来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演出事故’这种概念,也不懂专业的演出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甚至还有点觉得‘好刺激,做话剧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2016年,当时《九人》的舞美设计里有一个圆形的挂钟,演出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悬吊它的时候只用了一根线。这个钟是一个圆形的,线又很长,就没有办法完全固定。于是,台上一边演,这个钟就一边转。朱虹璇说:“那一年的戏讲的是一个报社的故事,大家从深夜一直讨论到黎明,有一些关于公平正义的探讨,也有正反两方的交锋。演出后,就有观众来问:这个挂钟的设计,是不是为了说明时间的流逝,以及是不是当主人公占优势的时候,这个钟就转到了正面,当这个钟转到背面的时候,就表示黑暗的力量占上风?观众会非常友善地去做解读,但这完全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做得很糙。现在想想,那时二十多岁,大家就是单纯想要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但还是愿意挤一点业余时间,请几天年假,出来做个戏。它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一个约定。至于这个作品本身的质量怎么样,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立得住的商业作品,当时我们的考虑都是比较肤浅的。”
幽暗48小时,带来“一转念”
剧团的转型在2017年。那年演出的作品当然也叫《九人》,写的是一个诊所里发生的故事。当朱虹璇事后再回忆那一年的意义,戏本身已经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幕后的故事给整个团队带来的影响。
这个戏的舞美,需要在舞台上布置五千多个药瓶。剧团预算捉襟见肘,请不起舞美工厂,也请不起装台工人。整部戏的舞美从设计到制作再到装台,全是剧团的人自己上手。“当时我们在北大找了一个地下室,剧团里的几十个人,不管是演员还是幕后,大家带着自己的亲属、男女朋友、志愿者、师弟师妹,在这个地下室里干了四十八个小时。工序非常复杂,要先给药瓶打孔,往里面装红纸片,然后往瓶子里穿线,穿完线以后要用热熔胶固定。最难的是进了剧场以后,要把这五千多个吊瓶挂在一个三米乘七米的大钢架上。没有阳光的地下室、黑黢黢的舞台,大家都在低头忙碌着。我在那个场景里,举目四望,突然就觉得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大家出于一份爱也好,出于老朋友的情谊也好,我们在这里用自己并不够专业的技能、消耗着并不够高效利用的时间,去完成一个最后也不是很完美,甚至比较粗糙的作品,我们做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从朱虹璇产生这个念头的那一刻起,剧团就开始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开始思考怎样更专业地去做一个作品,怎样经受住市场真正的考验,“作品是要能养活团队的,或者它至少可以负担本身的制作经费。”
“才刚立下这个宏图大志,紧接着的2018年我们就做了《落梅风》,成功地亏损了十几万。”朱虹璇笑言——“人生故事的起起伏伏,就是这样让人意想不到。”
当时想要把戏做得专业,所以剧团投入了很多去做舞美、灯光等。
“为了台上出现不到一分钟的打戏,我们请了一个武术指导,女演员路雯练了两三个月,每天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们还做了皮影的设计,这个戏里面所有的蒙太奇都是用皮影来表述的。从设计皮影的花样到把皮买回来,泡软、晒干,然后雕刻——所有的东西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演出的时候,幕后人员需要蹲在后台两个小时操作皮影,他们都吐槽说,为了做这个戏,他们已经快学会一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那一年的戏从成色上来说,进步了许多,也得到了更多观众的认可。当然也亏了很多钱,但我们的制作人自我安慰说,这叫战略投入。”
这一年,也是朱虹璇第一次做导演。“之前我只做编剧,那一年开始因为做了很多文本以外的尝试,让我觉得摸到一点导演这个工种的方法,也更加坚定了想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的信念。”
决心辞职做戏,转角遭遇疫情
之后“九人”迎来了2019年,这一年的原创作品叫《四张机》,也是剧团第八年的作品。
这个戏讲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老北大的几个教授——有的是保守派,有的是求新派,还有的是骑墙派,几个教授在评判四张卷子,为了决定一个录取名额,在会议室里吵了一整晚。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用民国题材去表达更多对于现代社会的思考,比如教育公平,比如为什么要有大学,或者在大学应该怎样兼容并包,求同存异。”
《四张机》是2019年“五四”左右的时候首演的,演到第三场的时候就开始一票难求了,后面基本上每一场都是满座。
《四张机》的成功,让朱虹璇冒出了一个新的念头:“我当时想这是不是老天爷给了我一个信号,告诉我终于可以全职出来做这件事情了。之前我们团队里,包括我在内,所有人都是百分之百兼职。”
朱虹璇之前在滴滴和腾讯都工作过,做的是战略咨询,“经常出差,飞来飞去,给客户做上市计划、产品定位、商业分析等,听上去很高大上的工作。”朱虹璇那些年的常态是:晚上加班到一两点,下班回到家还要再写剧本写到三点,早上又很早起来跟团队开方案会。
2019年的年底,朱虹璇终于决心辞职了。
然而,“你捋一下人类历史的时间线,就会发现我辞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月以后疫情暴发,全国的演出场所纷纷关停,持续了大概半年左右。2020年春天,本来安排好的《四张机》全国巡演,只能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取消。
于是,朱虹璇蹲在家里,继续开始写剧本。这一年,《春逝》诞生。
总在深夜,给我疗愈的故事
《春逝》讲述了民国时期几位物理学家抱团取暖的故事。其中一位女主角的原型是吴健雄,作为一位亚裔女性,她曾经做过美国物理学会的会长,也帮助研发原子弹,验证了“宇称不守恒”。
另外一个角色的原型,是当时中研院物理所的所长丁西林。朱虹璇说:“之前我只了解到他是一个剧作家,写过《酒后》《一只马蜂》《压迫》等作品,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他还是一个物理学家。”
在朱虹璇内心,《春逝》是一个“少数派抱团取暖”的故事,也是她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它总是在深夜的时候给我很多疗愈。”
然后就迎来了2021年的《双枰记》,这是“九人”第十年推出的作品,也是“九人”民国知识分子系列的第三部。枰,意思是棋盘,双枰就是两个棋盘。整部剧以下棋为线索,串联起了剧中人从青年到中年的二十年恩仇情义。
到了这一阶段,不管在剧本打磨还是舞台呈现上,“九人”都有了扎实的进步,也做出了更多的突破。
“看过我们戏的观众可能会知道,‘九人’的场刊向来都做得比较用心,而且都是免费的。《四张机》讲的是一个老北大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做了北京大学日刊,和1919年的报纸一模一样的制式。场刊上还有很多老北大的趣闻轶事,方便大家进剧场的时候提前了解人物。《春逝》讲的是物理所的故事,我们就把场刊做成了物理所丛刊。《双枰记》讲的是南京江宁地区监狱里的故事,所以我们的场刊就做成了南京的老地图。我托我一个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朋友,找来了故事发生那一年南京的真实地图,上面的每一条河、每一条街、每一条铁路,都是我们的设计师亲手画上去的。我们做了很多类似这样的细节性的工作,比如观众进场听到的每一首暖场音乐都和剧中的年代或者人物有关系,入场须知也都是演员们以角色的口吻去录的。”
2021年9月,《四张机》《春逝》《双枰记》三戏连演,在热门网络平台的评分分别是8.6、8.7和9.0。
非职业不等于不专业,最宝贵在“珍惜”
在演到第十年的时候,朱虹璇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非职业并不等于不专业。《双枰记》的五位演员没有一位是表演科班出身,都是所谓的“非职”演员。首演期间,有一件事让朱虹璇印象深刻:“我们一般是晚上七点半演出,按照工作流程,演员在此前化好装换好衣服,到台上来试麦就可以。但那天很早到了剧场,我就听见舞台上有声音。黑漆漆的舞台上,站了两位演员。他们在那儿默戏,站得笔直,从神情和眼神来看,肯定是在戏里的。他们在从头到尾地默着戏里的台词。舞台很黑,灯光昏暗,观众尚未入场,他们就在那里一默默了一两个小时。那一刻非常触动我,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职业演员一定比非职演员演得好。但其实很多说这话的人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初衷是多么重要。我们团队里这些演员,不管他们是职业的还是非职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极其珍惜这个舞台。”
戏里戏外“互文”,成就“拷问”的答案
虽然“九人”已经登上了更大的舞台,被更多的观众知道和关注,但对朱虹璇来说,“去年过得其实格外难熬,常常在疲倦,有时想放弃。”
想起当初在酒桌上立下“十年之约”时的快乐勇猛,朱虹璇觉得“惘惘如梦”:“真正走到第十年的时候,有很多成就感的来源已经被复制过了。第一次满场,我很兴奋,第一次豆瓣上8.0,我也很兴奋。但是后来再继续往下做的时候,幸福感的阈值在不断提升,感知到的更多是痛苦和挫败。回顾这过去的十年,竟不知是得多一点还是失多一点。剧团刚成立那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文艺女青年,觉得只需要把才华像星火一样撒在舞台上,它就会自然而然地长出很多参天大树来,不需要我们修炼太多的功课。但现在的我,必须在预算和现实的困难中摸爬滚打。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就在犹豫,这十年走完了,当年答应老朋友们要做的这件事情,我已经做到了,接下来我还要不要继续走这条不好走的路?”
恰在这样“自我拷问”的关口,一个朱虹璇从未想过会发生的瞬间出现在她眼前。
那一天排练厅里正好在排《春逝》,正排练到顾静薇和瞿健雄讨论要不要做粒子物理。顾静薇拉着瞿健雄的手,劝她不要去做,因为那在当时的行业阶段,这必然会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顾静薇:一个人的天赋不是无穷无尽的,漫长的时间会消磨掉你,消磨一天和消磨十年,不是一个概念!
瞿健雄:十年对一个人很长,但是放在整个人类历史或者学科的历史上就是短短的一瞬,十年,我能做的事情或许是结束了,但是物理的盛宴才刚刚开始。
顾静薇:没有老师,没有战友,也没有战壕,你还是要做这件事情吗?
瞿健雄:我还是要做这件事情。
“它是戏里戏外的一个奇妙的互文,那一刻窗外下着大雨,她们在排练厅说着这段对话,回答了我心里面那个还没来得及向任何人提出过的疑问。”朱虹璇说。
在“九人”十周年戏剧月期间,有很多观众会在留言墙上写留言。其中有两句话朱虹璇记得特别清楚:“九人不止九人,十年还有十年。”
【责编 宋伟】